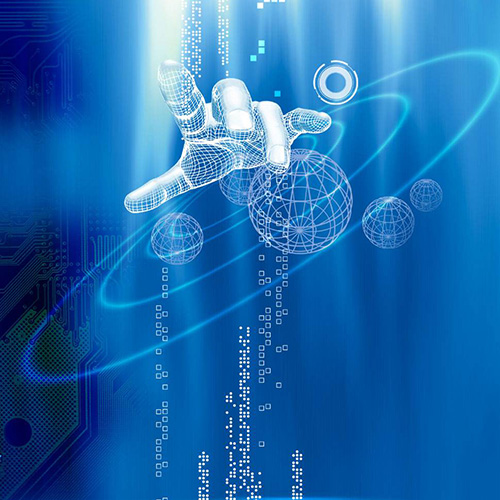近日,“卫生巾互助盒”火了,不断在微博、朋友圈、空间刷屏。
2020年10月14日,博主@梁钰stacey在微博分享了一位中学女教师给她的留言,该名女教师在教室里做了卫生巾互助盒,方便忘带卫生巾的女生使用。
(9).jpg)
卫生巾互助盒的想法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女生的响应,她们在经过校方许可之后于女洗手间设立卫生巾互助盒。截至10月29日,共有来自206所高校的学生自发参与其中。
(7).jpg)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卫生巾互助盒从最初一个简单朴素的小纸盒,发展为具备带壳塑料盒、防潮袋、说明标签的卫生设施,甚至还有高校制作了卫生巾自动售卖机。
这个活动再次将卫生巾议题带入舆论漩涡。有网友认为这是女权主义在作秀,也有人质疑将卫生巾互助盒放在厕所外是否真的能改善月经羞耻文化。
有强烈支持该活动并打算从高校推广到单位的热心人士;也有认为发起者“不害臊”、“不该把隐私问题拿出来占用公共资源”的反对声音;还有肯定活动的意义,但担心互助盒卫生安全状况并质疑其可行性的中立表达等。
除了互助活动本身,话题度最高的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中国政法大学里男厕外设立了“卫生纸自助盒”,暗示男性自慰也应该“去羞耻”。
(10).jpg)
另一件事是一位捐赠了卫生巾但在纸条上留言“我是女性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的男性,被指其话语背后暗藏着把女性视作不独立“附属品”的父权逻辑。
(13).jpg)
卫生巾虽小,却关乎天下女性最根本的生理问题,但在长期“月经羞耻”的文化压制下,卫生巾与月经问题始终缺少话语权。
不过,从援鄂医疗队的卫生巾问题,到数月前的“散装卫生巾”事件,再到现在的卫生巾自助活动,以卫生巾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正在努力构建以“拒绝月经羞耻”为突破口,关心女性切身利益的议题矩阵,以期在全社会范围内为争取女性的公共话语权而作出贡献。
卫生巾互助盒的杠杆力量
“米兔”反性侵运动、反堕胎法案、对冠性权的争论、张桂梅怒斥全职太太……近几年国内外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从来没有停止过。
(16).jpg)
这些话题涉及到的核心观点都涉及到“性骚扰”“教育资源分配”“职场性别歧视”“生育婚姻自由”等原则性的问题,它们多关注在既有社会规则中,女性受到的结构性压迫和父权压制,沉重又深刻。
其实卫生巾问题和月经羞耻近年来在网络舆论中一直都是平权运动的重要符号:四年前傅园慧面对镜头坦然表示自己来例假身体不舒服;雪莉生前在关爱女童运动中以捐赠卫生巾表达她的爱心;2020年国内多次关于卫生巾问题的舆论浪潮……
(11).jpg)
卫生巾体量很小,却能左右女性日常生活的体验,而这一决定女性过得是否舒适的重要元素却长期失语,被所谓的“文化传统”隐藏甚至污名化,例如网购卫生巾时默认“私密发货”;读书时男/女生对来月经一事的嘲笑等。
更糟糕的是,不少女性自己都将“月经羞耻”视作合理的“传统观念”。
因此,卫生巾互助盒的“撬动”意义才显得如此非凡,通过易于执行的操作,把女性对于“拒绝月经羞耻”的诉求清晰明确地表达在公共场合。做“小事”,大方说。
在活动中,卫生巾互助盒的背景纸上印有“拒绝月经羞耻”的字样,随着该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拒绝月经羞耻”的呼吁也再次得到了强化。女性们正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巧妙方式,更多人看到了卫生巾问题的重要性,她们渴望实现“拒绝月经羞耻”这一观念革新的勇气与决心也传达到了公共空间的大部分区域。
文章来自公众号“博卫传媒”,如侵权请联系删除